此文前,诚邀您点击一下“关注”按钮,方便以后第一时间为您推送新的文章,您的支持是我坚持创作的动力~
文|避寒
编辑|避寒
《——【·前言·】——》
她出生在法国,母亲一度决定不要她,父亲是国家副总理,母亲是全国妇联主席。
她却在新疆戈壁干过核研究,也为扶贫四处“求人”,她不是名人,却活得像一段冷门的共和国史。
特殊出身:革命家庭与颠沛童年
李特特出生于1923年,法国巴黎,那年她母亲蔡畅30岁,正在欧洲从事革命活动,腹中已怀数月。
党内有人劝她终止妊娠,革命优先,她动摇了,最终是自己的母亲葛健豪坚定反对。
葛健豪是老革命,清末女子,早年丧夫,一个人抚养几个孩子,她说:“不能断后。”
蔡畅生下了李特特,产后绝育,她说自己只有这一个孩子。
李特特从小跟着外婆,父亲李富春常年在党内负责经济工作,那时已经在苏联训练或从事地下工作,李富春和蔡畅聚少离多,大多数时间是凭信件联系。
李特特4岁那年,短暂回到上海,与父母团聚,住在法租界一栋楼里,常搬家,为了安全,她改姓改名,用“李青”“李英”这些普通名字在地下党系统中流动。
有一次警察查户口,家里藏了几本政治书,她被母亲迅速塞进床底,她不哭,只紧张地盯着天花板。
“你叫李特特吗?”“不是。”她说得很快,像背熟了答案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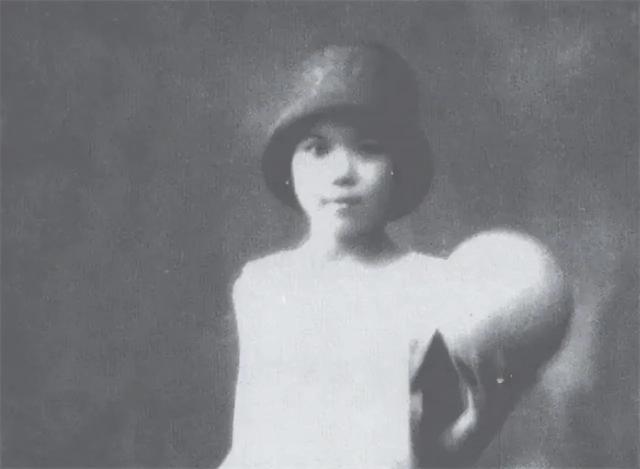
1938年,母亲将她送往苏联,苏联国际儿童院,专收中共党员子女,那时正是卫国战争前夕,儿童院条件艰苦,缺衣少食,冷得冻掉手指头。
她不再是“领导的女儿”,而是苏联国家培养的一名战时少年。
她学俄语、法语,每天训练,学开枪,学包扎伤员,16岁那年,被分配到战地医院,跟随医疗队转移到前线。
看到一个苏军士兵腿部中弹,被截肢前不断高喊“别动我刀带”,她听不懂词,但记得那条带子上缝着照片,那是他的家人。

17岁那年,她开始和成年人一起挖战壕、抬担架,身高不足1米6,体重不到45公斤,别人累倒,她接上去干,没人让她休息。
战争结束后,她没有留下,她决定回国,不是回家,是回到一个她只在记忆中听过、从未真正生活过的国家。
平凡奋斗:从北大荒到核效应研究
1953年,她回国,她没有进外交部、也没进清华北大,而是报了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。
她带着三个月大的儿子,去了北大荒,黑龙江三面是林场、冻土、蚊子窝,帐篷里一个炉子,一口锅,自己带娃,也干活。

她的丈夫是苏联人,在战争期间相识,回国后因为语言、生活方式、水土不服,矛盾频繁升级。最终离婚。
她一个人,在黑土地上种地、砍柴、喂牛、挑水、养孩子。
没有保姆,没有厨师,也没有任何人知道她是李富春的女儿,她从来没讲过。
一次组织上安排给她住砖房,她拒绝:“帐篷就行。” 住砖房就得调到机关,她不愿意。
三年后调往新疆,她被分配到核效应研究项目,地点在戈壁腹地。
她每天测量辐射数据,记录温度变化,穿着防护服,在沙地上埋电缆,太阳直射到仪器变形,晚上吃咸菜、压缩饼干、凉水煮的土豆。
她每天记数据,晚上写分析材料,时间一到就坐车回基地,不多说一句话。
有一次风沙太大,仪器零件吹飞,她沿风向走了近三公里捡回那个零件,没人知道她是谁,她也从不说。
1960年代,她被调回北京,进入中国农业科学院情报研究所。
她懂俄语、法语,没人教她翻译,没人教她怎么分类技术资料,她看外文期刊,看完就记录关键数据,自己整理参考书。
那时候没有检索软件,一本资料翻译完,要手写三遍,错一行,重来。
她参与编辑《国外农业科技资料摘要》《国外农业》系列书刊,每期上万字,翻译率达到95%以上。
她带的年轻同事说:“她的俄语是苏联原音,发音特别硬,听着像广播里的播音员。”
她不笑,常年穿一件灰色呢子外套,办公室里挂满旧地图、资料柜锁得紧紧的,她每天早上8点到岗,晚上7点下班,周末来加班,不报销餐费。
她不参加宴会,不参加聚会,她说:‘资料不能等,农业不能等。’
她是情报研究所的副研究员,但从未挂过“专家”头衔,很多研究报告最后写着:“翻译:李特特。”
晚年使命:扶贫“化缘”的争议与坚守
1988年,李特特退休,她没有搬进宽敞的离休宿舍,而是主动去扶贫基金会报到,那年,她65岁。
基金会刚成立,没预算,靠国家拨了10万元,几个办公室职员,连打印机都借用的。李特特成了常务理事,不领工资,负责筹钱。
没人教她怎么筹款,她拿出一个笔记本,在第一页写下“先找老同志”。她一个个打电话,一页页翻过去,圈出过去认识父亲的人,战友、企业家、前部级干部。
“我是李特特,李富春的女儿。”
“啊……你找我有事?”
“扶贫基金会,现在很困难,想请您帮帮忙。”
有人挂电话,有人说“最近手头紧”,有人直接说:“我帮你一次,不能总来找我。”
她还是一遍遍打,她说:“这些人以前都敬我父亲,现在都烦我,可扶贫不讲面子,讲成效。”
她说得不快,语气平淡,但咬字重。
一次去广东,她拜访一个企业家,对方没空,让秘书接待,秘书看她衣着朴素,不太上心。
她把材料拿出来,一页一页讲扶贫项目怎么做,哪个县、多少户、预算是多少,讲完,站起来:“麻烦转交,这次不捐也没关系。”
两天后,企业家打电话来,捐了20万元。
她背一个帆布包,里面是项目申请书、财政预算表、贫困户名单,包破了,缝补后继续用,她不请司机,自己坐公交,走访全国40多个贫困县。
有一次去甘肃天水,山路崎岖,汽车抛锚,司机说前面三公里没路,她下车走,鞋底磨平了,用胶带缠了脚掌。
到了村里,听村支书讲完情况,她记下户数、水源情况、缺口资金数,晚上住在村部,借一张竹席,把棉衣当被子。
扶贫款到账后,她不等人催,自己写报告寄去审计,每一笔都有记录,没一分钱模糊账目。
她说:“我不敢糊弄,怕对不起那些捐款人。”
后来有人笑她:“你是化缘的。”
她点头:“是啊,可不是给我,是给他们。”她指着照片上那些贫困户的孩子。
有人说她太执着,也有人背后议论她是“利用红色背景搞捞钱”,她听说了,不回应。
有一次内部会上,有年轻人说:“她搞不到钱的原因,是不会用手段。” 李特特没发火,只说了一句:“我只会用名单。”
1995年,她累积筹到超过1600万元资金,资助对象遍布40多个县,累计帮扶超过两万人,她拒绝挂名,不进先进名单,不出现在宣传栏。
她唯一接受的荣誉,是扶贫基金会“终身理事”,那张证书她贴在厨房门口,用胶布粘的。
精神传承:红色后代的另一种诠释
李特特一生,住在同一栋老房子里,80年代末,北京很多老干部搬进了新小区,有车有司机。
她仍住单位家属院,上下水老化,厨房小到只能放一口炉子,她说:“能用就不换。”
她有外婆葛健豪的照片,挂在卧室,葛健豪是早年赴法的革命者,变卖嫁妆资助共产党,晚年被称为“党的母亲”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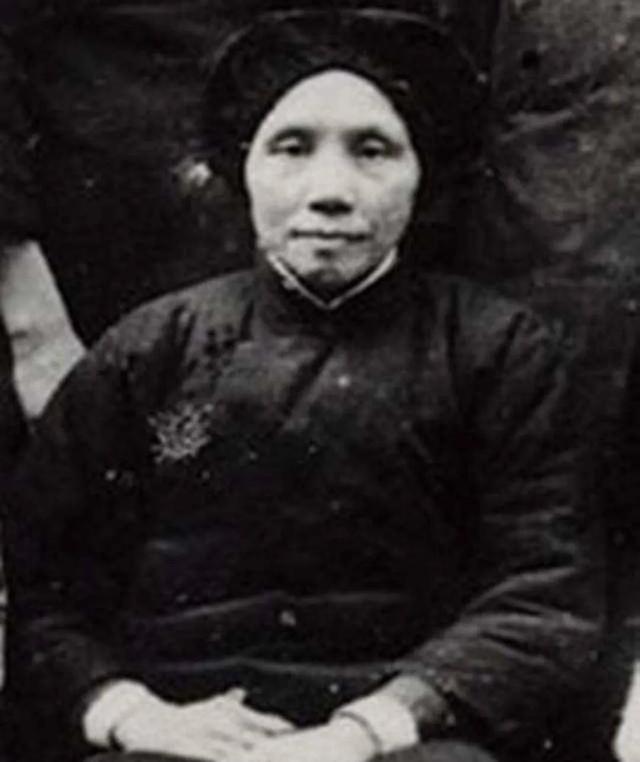
父母李富春和蔡畅,文革后恢复职务,晚年生活平静,李富春死前留下几件私人用品,全都上交国家。
她看到父亲留下的一张银行存单,金额不大,备注是“节余交党费”。
她从不向企业收“顾问费”,拒绝挂职,也不接受回馈。
一次福建某企业提出请她担任名誉董事,年薪30万元,她回绝,说:“我不是专家,更不能花我父亲的名声。”
她的老同事说:“她跟别的干部子女不一样,没那种官气,也没安全感。”
李特特病逝于2021年,98岁,没有追悼会,只在基金会贴了讣告。
她的遗愿,是不设灵堂,不送花圈,不留骨灰,她留下的衣物被打包捐给了一个残疾人康复机构。
她的事迹没有被大规模报道,只在内部刊物登过一篇短文,基金会一个年轻工作人员说:“我就是看她的事例才来扶贫的。”
她没有子女继承事业,丈夫早年离异,儿子多年在国外定居。
她活了一生,不靠父母,也不靠符号。
在那个笔记本最后一页,写着一行字:“别人看你做了多少,自己要看自己做得够不够。”
友情提示
本站部分转载文章,皆来自互联网,仅供参考及分享,并不用于任何商业用途;版权归原作者所有,如涉及作品内容、版权和其他问题,请与本网联系,我们将在第一时间删除内容!
联系邮箱:1042463605@qq.com